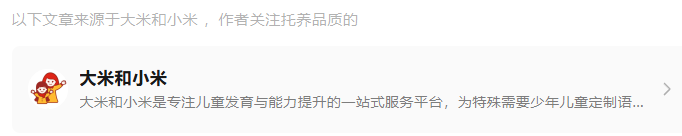

当我老了,我那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悬在无数特殊需要家庭心头的终极问题。
很多人在焦虑中等待,寄望于一个尚不明朗的未来;也有一些家长,选择主动出击,探索出一条通路。
禾禾爸爸就是这样一位“探路者”。他的儿子禾禾今年22岁,高二那年他突发的行为危机,让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也“逼”着他走上了自救之路。
2022年,他与另外九个特殊需要家庭,联合慧灵,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名为“慧灵家合”的大龄托养机构,以“社区化”和“正常化”的理念支持特殊需要家庭。他们的探索,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践样本。(为给自闭症孩子永久托养的“家”,9位家长决定买房自救)
近日,大米和小米和禾禾爸爸进行了一场对话,试图回答:在传统托养之外,我们能否为孩子创造一个既能获得专业支持,又能保留生活品质和个体尊严的未来?
以下是禾禾爸爸的口述。
整理 | Kido
编辑 | Zoey
图 | 受访者
孩子的变化,让我开始面对现实
我为孩子寻找出路,其实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现实危机。
禾禾是重度自闭症,伴随明显的挑战性行为。高二下学期,疫情停课半年后复学,他突然出现强烈情绪反应,用破坏行为表达“不想上学”,后来发展到在家不让别人进门、自己也抗拒外出。
那段时间非常艰难,我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孩子,必须有人替代家长进行日常照料和支持。我开始向其他家长请教,走访多家大龄服务机构,还曾与北京利智合作尝试日间服务班,就是想让孩子有机会走出家门,拥有更充实的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大龄家长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

比如,随着孩子长大,父母年迈,体力逐渐跟不上。禾禾上初中时,奶奶就已经照顾不了他了——因为他已经人高马大,老人无力应对。
更典型的是突发情况下的照护空缺。去年春节,一位29岁自闭症孩子的父亲突然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打电话问我孩子该怎么办。这个孩子近1米9,两百多斤,伴有情绪和攻击行为,当时北京几乎找不到能临时接收他的机构。
最后,我们慧灵家合的几位老师轮流加班,在春节期间照顾他,直到他父亲康复出院。
这种“突然之间无人接手”的困境,是我称之为“深度隐性需求”的现实——平时或许不明显,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就会瞬间浮现。而现实中,能提供相应支持的服务资源却非常有限。

大龄服务之所以难推进,是因为愿意付费的家长比例不高,而孩子个体需求差异巨大,难以形成规模化市场,导致基本上没有企业或个人愿意投资这一领域,目前主要依靠家长和公益力量艰难支撑。
据我估算,北京18岁以上的心智障碍人群可能超过两万,但实际能在机构接受日晚间服务的不足200人——只有1%-3%的家庭有需求或愿意付费购买服务。正是因为付费客户比例极低,整个行业难以发展。
北京市曾出台一项政策,对70岁以上老人与重度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养老机构的家庭给予补贴,每人每月最高2800元,相当于一家三口每月可获8400元支持,力度不小。但真正能落地享受此政策的案例极少。
我曾与北京一家四星级养老院深入探讨接收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可行性,但最终对方还是放弃了。主要原因包括:
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是多样化、支持型服务,与传统养老服务不同; 让二三十岁的自闭症患者与老年人共同生活,存在安全隐患。若分区管理,运营成本又会大幅增加; 培养能照顾自闭症成年人的专业护理人员,成本高、责任重,缺乏明确的责任和成本承担方。
因此,虽然政策上有空间,但现实中大龄孩子入住养老院仍困难重重。也有一些家长在探索父母与孩子能否在同一机构接受服务,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思考的方向。
不是“托养”,是支持他们好好生活
在我看来,“托养”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
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转变理念:大龄服务的核心不是“托”也不是“养”,而是支持他们过上“有品质的生活”。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被“养起来”,而是拥有丰富、有意义的生活。
当父母因体力、精力或时间限制无法持续提供支持时,专业机构或有经验的人可以接过这部分工作,让孩子在生活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继续在社区中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获得喘息的空间。
大龄特殊需要人士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与支持,而不是“修理”或“改造”。只要我们愿意提供适切的支持,他们同样可以过上有品质的人生。
慧灵家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建立——把孩子视为完整的“人”,尊重他们的权利与尊严。
我们坚持,大龄孩子应该在成熟的社区中生活,而不是被安置在偏远的郊区或农村。那种“找个小院圈起来”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隔离,是对他们平等权的剥夺。

把服务点设在城市社区,不仅是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也方便家人常来看望,维持情感联结。慧灵家合就位于北京大兴区五环内,是市内极少数能提供住宿的大龄社区服务机构之一。
现实是,许多机构不愿接收障碍程度重、有行为问题的孩子。因此我一直强调,情绪稳定、挑战行为少,是实现“好照顾”的基础。
台湾专家方武和李宝珍老师曾提出“四好青年”理念,即“好照顾、好家人、好帮手、好公民”。其中,“好照顾”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孩子身高一米八、体重两百斤,还有情绪行为问题,照顾难度将呈几何级增长。
我常常建议家长,从小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一个情绪稳定、行为可预测的孩子,哪怕没有语言和自理能力,也更容易获得支持。而一个有严重挑战行为的孩子,哪怕能力再强,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他的环境。
因此,家长切忌盲目“鸡娃”或过度训练。孩子小时候无法表达所承受的压力,缺乏支持的“融合”可能带来心理创伤,这些问题往往到成年阶段才会爆发,那时应对将更加困难。

在慧灵家合,我们致力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让家长得到喘息,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二是让孩子生活得愉快、充实,有同伴、有成就感,甚至能实现一些个人愿望。
我们曾接收过一个大脑损伤较重、每天必须穿纸尿裤的孩子。在这里生活两年多后,他逐渐摆脱了纸尿裤。
这并不是医学奇迹,而是因为老师给予他充分的关爱与接纳,伙伴之间氛围轻松,家庭式的环境让他放下了紧张。在这样的支持下,他的身心状态自然改善了。
还有很多孩子在这里尝试了人生的许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独自乘网约车回家,第一次独自在店铺购物。完成之后,他们脸上洋溢的自豪和喜悦,让我们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不是寻找第二个父母,而是分解责任
从2021年起,我开始组织家长沙龙,聚集了许多同行者一起探讨“我走了以后,孩子怎么办”。
我逐渐清晰,基本原则是:没有人能完全替代父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寻找“第二个父母”,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把照护责任分解给不同的人与组织。
具体来说,可以从三大方面着手:
最重要的是,家长要保持清醒,积极面对问题,而不是陷入抱怨或焦虑。现实中,真正需要长期全托服务的家庭并不多,大多数家长更需要的其实是“喘息服务”和应急支持。
要让孩子未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建议家长尽早从全生涯视角对孩子进行评估和预判。有机会可以多了解大龄服务的现状,甚至参与相关活动——有些年轻家长会来慧灵家合做志愿者,提前感受和学习,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在个人阅读方面,我推荐家长关注:
《残疾人权利公约》,了解基本权利框架; 《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未来安置探寻》(肖扬),深入浅出,贴近现实; 美国智能与发育障碍协会(AAIDD)的《智力障碍:定义、诊断、分类和支持系统》及《智能障碍与其他发展障碍者的品质生活》,这两本书系统构成了当代大龄服务的主流理念,强调“支持”而非“矫正”,注重生活品质而非单纯生存。
最后我想说,推动大龄服务没有捷径,现阶段仍需以家长自身力量为主,通过合作与实践,支持专业服务队伍逐渐成长。
我们每一位家长,都是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唯有更勇敢、更清醒、更团结,才能走得更远。
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变化、新的政策、新的实践出现。所以,请不要失去信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